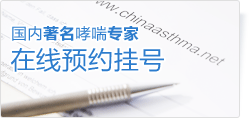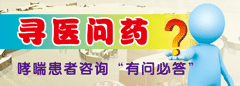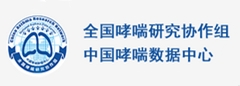哮喘——疾病?
2007/06/27
全世界大约有300,000,000人罹患哮喘,2025年预计将增加至4亿人。每250人中有1人死于哮喘。即使在发达国家哮喘也存在诊断和治疗不足。
什么是哮喘?这一名词起源于希腊语“aazein”,意思为“用嘴呼吸或喘息”,并首次出现于荷马史诗中。首次作为医学名词使用则可能是在希伯克拉底的著作中。中世纪Moses Maimonides在其“哮喘治疗”中提到哮喘症状往往由感冒诱发,并建议哮喘患者远离污浊的环境。19世纪这一名词很少在医学著作中被提及。20世纪初开始应用支气管扩张药物,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认识到气道炎症是哮喘发病的基础,从而引入激素治疗,并成为哮喘治疗的主体。但其后对哮喘发病机制,疾病触发因素、进展以及治疗反应的研究却出现停滞,同时由于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研究结果而陷入迷惘。 一些大规模的药物研究也受到定义不准确的影响,由于纳入标准,症状或疾病类型、严重度以及观察指标不同而无法进行比较。
1995年Fernando Martinez在Tuscon出生队列研究中描述了儿童期喘息或哮喘的不同表型,这一表型不会发展为典型哮喘。许多因病毒感染导致喘息的儿童在学龄期症状缓解,但目前还很难预测哪些患儿会发展为哮喘。因此幼儿期哮喘越来越多的被“学龄前喘息”所替代。
即便在成人,哮喘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这一点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Sally Wenzel 描述了一种区分不同表型或亚表型哮喘的方法,然而这些相互重叠的不同表型到底是同一病理过程不同时期的表现,还是由于不同的细胞或分子反应导致患者对不同的触发因素具有易感性呢?或者哮喘仅仅是多种不同的疾病共有的临床表现?直到19世纪发热都被认为是一种单独的疾病,也许过20,30或50年后我们对哮喘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表型”定义为由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导致生物体出现的不同特征。哮喘可能就是不同表型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由于符合临床上哮喘的诊断标准这些表型都被纳入哮喘的范畴中。只要具备相应的症状(喘息,胸闷或气急),伴有气道阻塞和可逆性气流受限,就可诊断为哮喘。尽管临床医生早已认识到哮喘存在着不同的表型,但一直没有发现区分这些表型的标记物,因此目前仍然对这些表型缺乏更好的理解。研究表明判断哮喘的表型有助于治疗。增加对哮喘表型的认识有助于深入理解各表型潜在的病理机制,还有助于将基因型与特定的病理特征相联系。
哮喘表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大部分应用大体的或临床的分类方法。过敏性和非过敏性哮喘是讨论最多的表型。哮喘表型划分为三大类:临床或生理标准分类;环境触发因素分类;病理生理分类,不同组别之间可能存在相互联系和重叠,每一表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临床或生理标准包括疾病严重程度,急性加重频率,是否存在慢性气流受限,哮喘发病年龄。对治疗不同反应如激素抵抗也纳入此分类。还可根据对特异出发因素如运动,环境抗原,职业性抗原或刺激物,药物(如阿斯匹林)以及menses。还可根据以不同类型的炎症为基础的免疫病理,特别是某些特定炎症细胞如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存在与否进行分类。但一种分类中的不同亚型还无法与其他分类中的亚型完全联系起来。因此尽管临床医生已经认识到以急性加重为主要表现的哮喘不同于以稳定的慢性气流阻塞为特征的哮喘,但这两种表型的免疫和病理特征还不清楚。许多证据支持这些表型存在着重叠。例如阿斯匹林哮喘一直被认为是哮喘的一种表型,同时阿斯匹林哮喘至少于两种临床亚型(严重型和成人发病型)以及一种病理生理亚型(血和气道高嗜酸性粒细胞型)有关。这些表型之间的相互转化可促进生物标记的研究,提高对表型的基因认识,提高对哮喘患者的个体化治疗。
译者按:
本文源自Lancet关于哮喘是否是一种疾病的争论,这一争论其实由来已久。近年来关于哮喘机制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同时带给我们的困惑也越来越多。一方面哮喘的发病机制中越来越强调气道炎症的作用,另一方面哮喘的诊断以及分级,分度仍以肺功能,气道高反应性为客观依据,而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尚有待考证。目前“一揽子”的治疗方案对大多数患者有效,但确实还有一部分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控制。1991年James教授就曾经提出如果把哮喘看作一个综合征,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疾病,就会重视对不同组别患者分别进行研究,而不是打包在一起进行研究,从而提高对患者的特异治疗,可惜十几年过去了,这一提议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马艳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 1000441 摘译)
A plea to abandon asthma as a disease concept
Anonymous
The Lancet; Aug 26-Sep 1, 2006; 368, 9537; Health & Medical Complete
pg. 705
Asthma: defining of the persistent adult phenotypes
Sally E Wenzel
The Lancet; Aug 26-Sep 1, 2006; 368, 9537; Health & Medical Complete
pg. 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