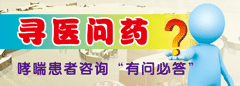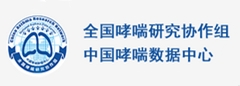微生物组学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017/11/30
沈宁 贺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科 10019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科 100191
人体微生物群(microbiota)是指在人体共生或致病的全体微生物,微生物组(microbiome)指全部微生物的基因组,即检测到人体各部位微生物群落的宏基因组序列,其中每个序列代表独立的微生物,通过对序列集合的分析得到的微生物种类及其丰度。微生物组学的研究可以加深对人体微生物种群结构、人与微生物交互作用、人体微生物功能差异、微生物和疾病等问题的理解。人体皮肤、口腔、咽喉、阴道和胃肠道等黏膜表面存在大量的微生物,并在疾病发展中起重要作用[1]。美国2007年启动了人类微生物组学项目(The Human Microbiome Project, HMP),旨在研究人体微生物群及其与人类疾病和健康的相互关系[2,3]。其中研究最充分的是肠道,在人体肠道内,有数千亿计的微生物群,包含多达15 000种以上的细菌,其基因总和约是人类基因量的100倍以上,对人体的生理代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是人体内的一个“新系统”或“新器官。
由于传统观点认为下呼吸道是无菌的,因此未被纳入最初的HMP项目。尽管后来发现健康者肺内也存在微生物群[4],但是目前对于肺微生物组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胃肠道领域。近年来,已经开展了下呼吸道微生物组学和哮喘、囊性纤维化等疾病关系的研究,建立了标本采集技术等方法学,初步了解了健康人以及部分慢性气道疾病患者呼吸道微生物组学的主要特征和差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相关微生物组学的研究是新近才受到关注的领域,本文特对此进行综述和讨论。
一、健康人呼吸道微生物组学
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下呼吸道是有菌的,有大约70%以上的细菌不能用传统的培养方法培养[5,6],其他20-30%培养难度也很大[7],基于识别细菌特有的核糖体RNA技术为进一步研究微生物组学提供了可能。近年来通过高通量测序研究发现不同健康个体的呼吸道微生物群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在门水平最常见的是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拟杆菌(Bacteroidetes);在属水平,假单胞菌(Pseudomonas)、链球菌(Streptococcus)、普雷沃菌(Prevotella)、梭杆菌(Fusobacteria)、和韦荣球菌(Veillonella)占主要地位,潜在致病的病原体包括嗜血杆菌(Haemophilus)和奈瑟菌(Neisseria)相对较少。
不同测序方法和采样部位可影响微生物组的结果,目前发表的文献多为单中心小样本的研究,采用的标本包括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BAL)、保护性毛刷标本、肺组织标本、诱导痰标本和下呼吸道抽吸物的标本。采样部位不同得到的微生物组群的结果也不同,同时可能受到经鼻、经口支气管镜时上气道的污染以及镇静时误吸等因素的影响。Morris等[8]收集了64名吸烟及非吸烟的健康志愿者口咽部标本和肺泡灌洗液,采用16S rRNA测序技术分析,发现上、下呼吸道微生物组大多数存在同源性,仅仅是数量上有差异,比如在下呼吸道有更丰富的肠杆菌和嗜血杆菌等。下呼吸道菌群总量减少的原因可能是纤毛规律性摆动,将大多数细菌排出气道所致。对健康人群微生物组学的研究是进一步研究疾病状态下微生物组学的基础。
二、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下呼吸道微生物组学的变化
慢阻肺居全球慢性病死因的第四位,其特征是持续性气流受限,呈进行性发展,与气道和肺组织对烟草烟雾等有害气体或颗粒的慢性炎症反应增强有关[9]。在发达国家,导致慢阻肺的主要原因是吸烟,而在发展中国家,来源于生物燃料的室内空气污染也起重要作用。目前并不清楚为什么只有部分吸烟者发展为慢阻肺,同时也不清楚为什么有的不吸烟者也会发展为慢阻肺。
细菌感染在慢阻肺的发病和急性加重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依靠传统的细菌培养模式,难以获得准确的下呼吸道微生物组信息。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都是以培养为基础的技术,发现稳定期慢阻肺患者主要的定植细菌是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下呼吸道细菌定植可能是导致慢阻肺反复急性加重的原因之一,与气道慢性炎症等密切相关,但稳定期常规培养的阳性率不足30%。Sethi等采用BAL标本比较了26例吸烟已戒的稳定期慢阻肺患者、20例吸烟已戒的非慢阻肺者和15名健康的非吸烟者下呼吸道微生物群的情况,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稳定期慢阻肺患者可培养获得潜在致病细菌,而戒烟的非慢阻肺没有发现潜在的致病细菌,健康非吸烟者中仅一名可培养出潜在致病细菌[10]。其他数项支气管镜采样的研究采用的也是以培养为基础的技术,并得到相似结果,即约30%的稳定期慢阻肺患者在远端气道存在潜在的致病细菌。最常见的致病细菌是流感嗜血杆菌,部分慢阻肺患者也培养到肺炎链球菌、卡他莫拉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由于不能更细致全面地观察菌群变化,因而细菌定植在COPD发病和疾病进展中的作用尚缺乏深入研究。
应用检测细菌16S rRNA测序技术,是研究慢阻肺下呼吸道微生物群的里程碑式的进展,成为近年来慢阻肺疾病机制的研究热点。Hilty等[11]研究了5名慢阻肺患者鼻、口腔和支气管毛刷的微生物组学,发现慢阻肺患者气道微生物群和8名对照组相似,和健康对照相比,慢阻肺患者变形菌门更常见,而拟杆菌门少见。Erb-Downward等[12]收集了7名正常吸烟者、4名慢阻肺患者和3名健康对照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进行分析,发现三组患者在细菌拷贝数方面没有差异,但3组之间的细菌种类有重叠,同时中度慢阻肺患者的细菌菌群多样性下降,研究者提出可能存在肺“核心”微生物菌群,75%以上的标本包括假单胞菌、链球菌、普雷沃菌和梭杆菌,而一半以上的标本中还可发现嗜血杆菌、韦荣球菌和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Pragman等[13]采用22例慢阻肺患者和10例健康对照者的BAL进行研究,发现口腔菌群可能是下呼吸道微生物群的来源。Cabrera-Rubio等[14]通过对慢阻肺患者的痰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和支气管黏膜活检等区域样本测序,发现链球菌、普雷沃菌、莫拉菌、嗜血杆菌、不动杆菌、梭杆菌和奈瑟菌最常见,痰标本的微生物群的种类不同于远端支气管(BAL、支气管活检)标本的微生物群,而BAL和支气管粘膜活检的细菌组成类似。Erb-Downward等采用移植后切除的肺组织进行研究,主成分分析显示以假单胞菌、嗜血杆菌和窄食单胞菌(Stenotrophomonas)为主。Sze等[15]对非吸烟者、吸烟非慢阻肺者和重度慢阻肺患者远端肺组织的微生物组学进行了研究,发现细菌数多于对照组,厚壁菌门显著增多,其中以乳酸菌属(Lactobacillus)增多为主。以上研究结果提示,除常规培养发现的细菌外,在COPD患者的肺组织和气道内确实存在一些过去不曾检出的细菌,而这些菌种导致的菌群变化或许与疾病进展相关。由于BAL和支气管粘膜活检的细菌组成类似,通过采集气道内标本来研究菌群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就具有了可行性。
现有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慢阻肺患者微生物组学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可能与检测方法、采样部位和方法等有关。但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慢阻肺患者肺部细菌量和健康人相似,重度慢阻肺患者下呼吸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下降,变形菌门数量增多。由于大部分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是由细菌感染诱发的,因此,这种改变可能是细菌性急性加重的后果。此外,在急性加重期抗菌药物治疗后,下呼吸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下降;随着病情加重和持续时间延长,其多样性进一步下降。然而,尚无研究明确表明慢阻肺患者下呼吸道和肺内微生物组多样性下降是导致特定细菌过度生长或细菌负荷上升的原因。
Molyneaux等[16]在稳定期轻度慢阻肺患者诱发实验性鼻病毒上呼吸道感染,并探讨了鼻病毒感染对呼吸道微生物群的影响。结果显示部分慢阻肺患者在鼻病毒感染15天后诱导痰中的细菌拷贝数增加了6倍,原有微生物群中流感嗜血杆菌显著过度生长,这种变化可持续到病毒感染后42天;相比之下,非慢阻肺或吸烟者均未出现类似变化,提示COPD患者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后更易于合并细菌感染另外,并非所有患者在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后均出现菌群改变,这种个体差异可能是慢阻肺“频繁急性加重”表型的原因之一。
三、慢阻肺急性加重下呼吸道微生物组的变化
慢阻肺急性加重定义为呼吸道症状的急性恶化,导致需要额外治疗。急性加重是导致健康状态恶化、气道和全身炎症反应加重以及肺功能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细菌感染在急性加重中占有重要地位。常规培养技术显示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肺炎链球菌是常见引起急性加重的细菌,重症的慢阻肺患者,铜绿假单胞菌也较为常见。但是,由于稳定期也存在这些细菌的定植,因此急性加重可能不单纯是细菌的存在。病原微生物和宿主的交互作用成为研究的热点。关于AECOPD的微生物组研究显示无论是稳定期还是急性加重期慢阻肺患者的微生物组都存在高度异质性,例如,部分慢阻肺患者在急性加重初期出现流感嗜血杆菌或卡他莫拉菌显著增加,而其他患者仅出现轻微的变化。“细菌性表型”的慢阻肺急性加重以变形菌门为主,而“嗜酸粒细胞性表型”的慢阻肺急性加重以厚壁菌门为主[17]。同时,慢阻肺急性加重期不同治疗药物如糖皮质激素和抗菌药物对患者的微生物组组成和数量均有不同的影响[18]。
四、慢阻肺下呼吸道微生物组学的临床意义
下呼吸道微生物组学领域的研究尚处于早期阶段,且下呼吸道菌群负荷低、早年研究标本采集难以避免口腔和/或鼻咽部菌群污染等因素,目前仍无直接证据证实下呼吸道微生组学的变化和慢阻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已有数据显示其能影响慢阻肺的发生发展。
稳定期慢阻肺患者下呼吸道不仅可以定植潜在的致病菌,更为重要的是和非定植慢阻肺患者、戒烟非慢阻肺患者、健康非吸烟者相比,痰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细胞因子或趋化因子在有细菌定植的慢阻肺患者显著增高,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8(IL-8)、白三烯B4和中性粒细胞及中性粒细胞降解产物水平,如髓过氧化物酶(MPO)、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等[19]。同时MPO水平还会随定植菌水平增加而增高。不同定植菌对气道炎症影响程度也不相同,分别检测有流感嗜血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卡他莫拉菌定植的慢阻肺患者痰MPO活性,结果显示铜绿假单胞菌定植患者痰中MPO活性最高,而在卡他莫拉菌定植患者MPO活性最低。因此,细菌定植并非简单的与人共生共存, 它至少具有2个方面的作用[20]:诱导机体的炎症细胞和结构细胞产生更多的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吸引更多炎症细胞到达病变部位,使炎症反应增强和持续;破坏原有组织结构,参与慢阻肺的慢性炎症过程。同时,定植菌也可以启动特异性获得性免疫反应,表现为肺组织局部出现B细胞淋巴样滤泡及黏膜、血清IgG抗体产生。
除了肺微生物组对慢阻肺发病机制的潜在作用之外,肠道微生态可能也会对肺发生影响。例如,吸烟和戒烟均可明确引起肠道微生态变化[21],而炎症性肠病是慢阻肺的众多合并症之一[22],因此,吸烟可能通过影响肠道微生态并进而导致系统性炎症和相关疾病。
五、未来研究方向
人类下呼吸道微生物群的发现和技术的进步为认识慢阻肺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近的研究结果将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其和慢阻肺的相关性,这将有利于发现新的慢阻肺治疗方法[23]。目前关于慢阻肺下呼吸道微生物组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环节等待完善,如需要多中心、大样本试验,对多种相关因素展开独立分析和开展进一步纵向研究,即通过对同一群患者长期随访,描述出慢阻肺发生、进展及急性加重过程中下呼吸道微生物组的动态变化,以及下呼吸道微生物组失调是否加快慢阻肺疾病进展。因此总体上慢阻肺患者微生物组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下呼吸道微生物群在疾病中的作用还远未阐明。
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下呼吸道微生物组多样性的改变可能和慢阻肺的发生、进展以及急性加重相关,未来对于慢阻肺的治疗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下呼吸道微生物组,甚至移植正常菌群,也许会延缓慢性气道炎症的进展,甚至逆转疾病的进程。
参考文献
1.Relman DA. Microbiology: learning about who we are. Nature, 2012, 486: 194-195.
2.Human Microbiome Project Constortium. Structure, function and diversity of the healthy human microbiome. Nature, 2012, 486: 207-214.
3.Human Microbiome Project Constortium. A framework for human microbiome research. Nature, 2012,486:215-221.
4.Huang YJ, Charlson ES, Collman RG, et al. The role of the lung microbiome in health and disease. A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workshop report.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3, 187:1382-1387.
5.Suau A, Bonnet R, Sutren M, et al. Direct analysis of genes encoding 16s rRNA from complex communities reveals many novel molecular species within the human jut.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99, 65: 4799-4807.
6.Hayashi H, Sakamoto M, Benno Y.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he human gut microbiota using 16s rDNA clone libraries and strictly anaerobic culture-based methods. Microbiol Immunol, 2002, 46:535-548.
7.Sibley CD, Grinwis ME, Field TR, et al. Culture enriched molecular profiling of the cystic fibrosis airway microbiome. PLoS ONE, 2011, 6:e22702.
8.Morris A, Beck JM, Schloss PD,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respiratory microbiome in healthy nonsmokers and smokers.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3, 187: 1067-1075.
9.Vestbo J, Hurd SS, Agusti AG, et al.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GOLD executive summary.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3, 187: 347-365.
10.Sethi S, Maloney J, Grove L, et al.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bronchial bacterial colonization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6, 173: 991-998.
11.Hilty M, Burke C, Pedro H, et al. Disordered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asthmatic airways. PLoS ONE, 2010, 5:e8578.
12.Erb-Downward JR, Thompson DL, Han MK, et al. Analysis of the lung microbiome in the “healthy” smoker and in COPD. PLoS ONE, 2011, 6: e16348.
13.Pragman AA, Kim HB, Reilly CS, et al. The lung microbiome in moderate and sever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LoS NOE, 2012, 7: e47305.
14.Cabrera-Rubio R, Garcia-Nunez M, Seto L, et al. Microbiome diversity in the bronchial tract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J Clin Microbiol, 2012, 50: 3562-3568.
15.Sze MA, Dimitriu PA, Hayashi S, et al. The lung tissue microbiome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2, 185: 1073-1080.
16.Molyneaux PL, Mallia P, Cox MJ, et al. Outgrowth of the bacterial airway microbiome after rhinovirus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3, 188: 1224-1231.
17.Gomez C, Chanez P. The lung microbiome: the perfect culprit for COPD exacerbations? Eur Respir J, 2016; 47: 1034–1036.
18. Huang YJ, Boushey HA. The Sputum Microbiome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erbations. Ann Am Thorac Soc, 2015, 12, S176–S180.
19. Banerjee D, Khair OA, Honeybourne D. Impact of sputum bacteria on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health status in clinical stable COPD. Eur Respir J, 2004, 23: 685-691.
20.沈宁, 贺蓓. 细菌感染与免疫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和疾病进程中的作用. 中华医学杂志, 2012, 92: 941-942.
21.Biedermann L, Zeitz J, Mwinyi J, et al. Smoking cessation induces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humans. PLoS ONE, 2013, 8: e59260.
22. Keely S, Talley NJ, Hansbro PM. Pulmonary-intestinal cross-talk in mucosal inflammatory disease. Mucosal Immunol, 2012, 5: 7-18.
23.Dickson RP, Martinez FJ, Huffnagle GB. The role of the microbiome in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lung disease. Lancet, 2014, 2014, 384: 691-702.